来源:北京日报
本月,刘一达的新京味儿话剧《玩家》将在人艺建组开排;2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红案白案》也将在《小说月报》连载。关于京味儿文化,他一直是边学边用、边用边学,也因此有了自己独到的体悟与见解。他自言,守着北京文化的富矿,挖了一辈子,越挖越感觉太有的挖了。
猛学新词儿
不能用古董语言写当下小说
刘一达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40多年来他一直熟稔地运用老北京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先后推出了《故都子民》《胡同根儿》等一批讲述老北京文化的作品。
这一切都源于他少时的“偷艺”。16岁时,他成为北京市土产公司下属木制品厂烧炭车间的一名烧炭工,结识了车间内五行八作的老师傅,“有古玩商、天桥艺人、小商贩、洋车夫……”师傅们讲的那些老北京掌故轶闻、奇谈怪事,成为他日后创作的丰富素材,也开启了他对老北京文化由内而外的热爱。
上世纪90年代,刘一达成为《北京晚报》记者。传说,报社编辑部有两位大咖,从业多年始终保持手写的习惯,一位是评论家苏文洋,另一位就是刘一达。三年前,这个传说被改写了。那年,退了休的刘一达学会了用电脑写作。去年,他又开通了微信。
“微信进入人们的生活以后,一场北京话的革命到来了。”刘一达感慨道。从前的北京土话地域性很强,许多词汇是北京特有的。但在网络时代,网友使用语言的地域性不再那么鲜明,语言呈现出高度交汇融通的特点。“再用古董一样的语言写现在的小说,肯定不行了啊。”他说,许多老北京话,现在的人们已经听不懂也用不上了,如果自己跟不上趟,文学上的沟通恐怕会出问题。
每天甭管干什么,刘一达手边都得有个小本本,专门记他听到、看到的新鲜词儿,比如打飞的、段子手、拼友、舔屏、小鲜肉、违和感……
新作《红案白案》
早年“臊干”是如今“键盘侠”
刘一达的小本本如今已经记了20多本,他的写作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最新长篇小说《红案白案》。
“新京味儿的新,在内容上表现为反映现实、反映当下,在语言上体现为具有当下时代特色的语言;至于文章叙事方式,也得符合现在读者的阅读习惯。”刘一达说。
红案和白案,是指厨师的分工。简单点说,白案做面食,红案做肉食。早年当记者时,刘一达曾采访过两位老厨师,一位是清代皇宫御膳房老师傅的徒弟,另一位则称自己祖上曾在御膳房工作。报道刊发之后,刘一达发现其中一位厨师在接受采访时说的很多信息不实,这也给了他一次警醒,清代皇宫内的膳单上到底记载了哪些饮食?现在市面上那么多号称“宫里”传出来的菜,到底真实与否?均值得考证。
“于是我就想写一部御膳房题材的作品,以正视听。”刘一达说。为了让故事建立在准确的细节之上,他想尽办法进入到明清两代皇家档案馆皇史 ,一页一页查找膳单。这部小说,一写就是五年。长篇小说毕竟不是民俗读本,终究还是要写人物的命运,刘一达于是将笔触落脚于两家御膳房师傅的后代在当今社会的争与不争。
,一页一页查找膳单。这部小说,一写就是五年。长篇小说毕竟不是民俗读本,终究还是要写人物的命运,刘一达于是将笔触落脚于两家御膳房师傅的后代在当今社会的争与不争。
刘一达说,北京土话中有个词儿叫“臊干”,指代一种人:不干正经事,却总是气人有笑人无,整天品天论地、牢骚满腹。“小说中的两位御膳房师傅,代表两户人家、两类心态、两种命运。一家勤勉干事业,另一家则是典型的‘臊干’。”刘一达说,这样的人物以前有,现在依然有,只不过“臊干”的称呼演变成了“键盘侠”或其他名词。
研究北京话
“死”“吃”有40余种表达
在长篇小说《红案白案》之外,前不久刘一达还完成了历时七年创作的话剧剧本《玩家》。6月25日,该剧即将在人艺建组,8月末将与观众正式见面。这部剧浓缩了他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与王世襄、耿宝昌、朱家 、马未都等新老几代收藏家共同“玩儿”文玩的经历,也蕴含了他对老北京玩家们捡漏、打眼、洒金、洗货等传奇故事的观察与理解。
、马未都等新老几代收藏家共同“玩儿”文玩的经历,也蕴含了他对老北京玩家们捡漏、打眼、洒金、洗货等传奇故事的观察与理解。
眼下,他又忙活起撰写专门研究北京话变迁的作品,“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用北京土话写作多年,自然想要更深入地研究这门学问。”虽然北京话就是他创作的工具,可一旦细研究,仍然会有许多惊喜,“北京话属于中原音系,又融合了蒙语、满语、山西语言特色,其词汇量异常丰富,带有一定的幽默感和含蓄性。”他举例说,仅仅关于“死”,北京话就有40多种表达方式:去了、走了、挂了、回去了、咽了气了、弯回去了、听蛐蛐叫去了、去了八宝山了、去大烟囱胡同了……关于“吃”,也有40多种表达方式,可见词汇量之大。除了词汇,年轻人说话的发音变化,也没逃过他的耳朵,“现在人们说话越来越爱吞字,比如‘国安’常说成‘关’,这渐渐也派生出一些新的语言现象。”
除了写作、搞研究,刘一达还有不少社会活动,在他家里客厅的台历本上,差不多每个日期格里都用粗黑的笔记着讲座预约。他的讲座围绕京味儿、北京文化展开,而最近一年来则集中于“老北京规矩”,“请安、问起儿、早起一杯茶、吃饭不能吧唧嘴等老规矩,依然被人们重视,依然被人们自觉自愿地想要传承。”(李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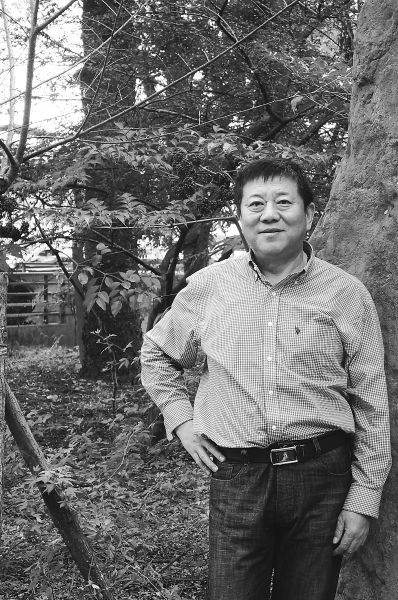
本月,刘一达的新京味儿话剧《玩家》将在人艺建组开排;2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红案白案》也将在《小说月报》连载。关于京味儿文化,他一直是边学边用、边用边学,也因此有了自己独到的体悟与见解。他自言,守着北京文化的富矿,挖了一辈子,越挖越感觉太有的挖了。
猛学新词儿
不能用古董语言写当下小说
刘一达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40多年来他一直熟稔地运用老北京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先后推出了《故都子民》《胡同根儿》等一批讲述老北京文化的作品。
这一切都源于他少时的“偷艺”。16岁时,他成为北京市土产公司下属木制品厂烧炭车间的一名烧炭工,结识了车间内五行八作的老师傅,“有古玩商、天桥艺人、小商贩、洋车夫……”师傅们讲的那些老北京掌故轶闻、奇谈怪事,成为他日后创作的丰富素材,也开启了他对老北京文化由内而外的热爱。
上世纪90年代,刘一达成为《北京晚报》记者。传说,报社编辑部有两位大咖,从业多年始终保持手写的习惯,一位是评论家苏文洋,另一位就是刘一达。三年前,这个传说被改写了。那年,退了休的刘一达学会了用电脑写作。去年,他又开通了微信。
“微信进入人们的生活以后,一场北京话的革命到来了。”刘一达感慨道。从前的北京土话地域性很强,许多词汇是北京特有的。但在网络时代,网友使用语言的地域性不再那么鲜明,语言呈现出高度交汇融通的特点。“再用古董一样的语言写现在的小说,肯定不行了啊。”他说,许多老北京话,现在的人们已经听不懂也用不上了,如果自己跟不上趟,文学上的沟通恐怕会出问题。
每天甭管干什么,刘一达手边都得有个小本本,专门记他听到、看到的新鲜词儿,比如打飞的、段子手、拼友、舔屏、小鲜肉、违和感……
新作《红案白案》
早年“臊干”是如今“键盘侠”
刘一达的小本本如今已经记了20多本,他的写作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最新长篇小说《红案白案》。
“新京味儿的新,在内容上表现为反映现实、反映当下,在语言上体现为具有当下时代特色的语言;至于文章叙事方式,也得符合现在读者的阅读习惯。”刘一达说。
红案和白案,是指厨师的分工。简单点说,白案做面食,红案做肉食。早年当记者时,刘一达曾采访过两位老厨师,一位是清代皇宫御膳房老师傅的徒弟,另一位则称自己祖上曾在御膳房工作。报道刊发之后,刘一达发现其中一位厨师在接受采访时说的很多信息不实,这也给了他一次警醒,清代皇宫内的膳单上到底记载了哪些饮食?现在市面上那么多号称“宫里”传出来的菜,到底真实与否?均值得考证。
“于是我就想写一部御膳房题材的作品,以正视听。”刘一达说。为了让故事建立在准确的细节之上,他想尽办法进入到明清两代皇家档案馆皇史
刘一达说,北京土话中有个词儿叫“臊干”,指代一种人:不干正经事,却总是气人有笑人无,整天品天论地、牢骚满腹。“小说中的两位御膳房师傅,代表两户人家、两类心态、两种命运。一家勤勉干事业,另一家则是典型的‘臊干’。”刘一达说,这样的人物以前有,现在依然有,只不过“臊干”的称呼演变成了“键盘侠”或其他名词。
研究北京话
“死”“吃”有40余种表达
在长篇小说《红案白案》之外,前不久刘一达还完成了历时七年创作的话剧剧本《玩家》。6月25日,该剧即将在人艺建组,8月末将与观众正式见面。这部剧浓缩了他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与王世襄、耿宝昌、朱家
眼下,他又忙活起撰写专门研究北京话变迁的作品,“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用北京土话写作多年,自然想要更深入地研究这门学问。”虽然北京话就是他创作的工具,可一旦细研究,仍然会有许多惊喜,“北京话属于中原音系,又融合了蒙语、满语、山西语言特色,其词汇量异常丰富,带有一定的幽默感和含蓄性。”他举例说,仅仅关于“死”,北京话就有40多种表达方式:去了、走了、挂了、回去了、咽了气了、弯回去了、听蛐蛐叫去了、去了八宝山了、去大烟囱胡同了……关于“吃”,也有40多种表达方式,可见词汇量之大。除了词汇,年轻人说话的发音变化,也没逃过他的耳朵,“现在人们说话越来越爱吞字,比如‘国安’常说成‘关’,这渐渐也派生出一些新的语言现象。”
除了写作、搞研究,刘一达还有不少社会活动,在他家里客厅的台历本上,差不多每个日期格里都用粗黑的笔记着讲座预约。他的讲座围绕京味儿、北京文化展开,而最近一年来则集中于“老北京规矩”,“请安、问起儿、早起一杯茶、吃饭不能吧唧嘴等老规矩,依然被人们重视,依然被人们自觉自愿地想要传承。”(李洋)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