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文好书
张者:用文学的光芒照亮法律的黑暗角落
《桃夭》是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要找个批评家审读,就找到孟繁华老师,他给我提了3000字的意见,我看了修改意见有点犯傻,在床上打滚,思考着这怎么改呀,然后又给孟繁华打电话,在电话交流中我突然豁然开朗,也就是说他把我这盏灯点亮了,后来稿子经过了一次大的改动。当然,目前看来《桃夭》还有修改的余地,其实,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每一本书总是要留下一点遗憾,不留下一点遗憾,今后的写作怎么完美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了今后的完美,就暂时留下点遗憾吧。
不过,我还是想就各位老师的一些看法回答如下:
1、 关于小说中的巧合。在写作中我确实采用了一些巧合,采用这些巧合时我当然不能用所谓的“无巧不成书”来安慰自己,我也知道情节的过分巧合可能降低故事的可信度,从而消解小说的艺术性,可是我还是采用了很多巧合,我的目的恰恰不是为了让读者可信,是为了让读者不信,在不可信中产生一种荒诞感。其实,所有的巧合都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时发生。比方:我叫张波,我在读大学时曾经认识了一位也叫张波的女生,我们两个差点成为恋人,如果成为了恋人,而且还结了婚,生了孩子我肯定起名叫张小波。看吧,这是发生在我自己生活中的事,这很巧合,巧合得已经不可信了,就达到了荒诞的效果。
请不要把我的作品当纯粹的现实主义作品来阅读。巧合的极致就荒诞,荒诞的极致是魔幻。我想完成一种城市的荒诞现实主义。对,就命名为荒诞现实主义吧。
2、 关于人称叙述。有人认为小说中的这个“我”身份没有严格遵守叙事视角的客观性,如一个幽灵的存在。其实,这种叙事方式不是我的首创,早在80年代莫言先生在《红高粱》中就采用了这种叙事方式,我奶奶,我爷爷……按照叙事视角的客观性原则,就视角来说,我怎么能看到我奶奶和我爷爷过去的事情?猛一看是第一人称叙述,其实又不是第一人称叙述,说是第三人称叙述,又时不时出现一个“我”。这个“我”有时在情节中存在,有时又不在情节中。我把这种叙述方式叫“双人 称”叙述方式。
张者:用文学的光芒照亮法律的黑暗角落
早在《桃李》的写作中,我就采用这种方式了,当时也有朋友和我探讨过这种叙述,会不会有悖叙述伦理。《桃夭》的主要叙述人“我”是五个师兄弟中的一位,但叙 事视角并不仅仅停留在“我”这里,而是在“我”和五个师兄弟之间互相自由地转换。“我”似乎游离于圈子之外,又似乎不断地介入到每一个切身感受当中,与他们交谈,与读者对话。通读整部小说,“我”似乎是一位能穿梭时空的叙述者,“我”的叙述可以穿越历史,回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个纯真诗意的理想年代,并在历史和现实中自由穿行。毫无疑问,这叙述方式使得小说的叙述背景更为辽阔深远,使人物更加立体丰满,能更好地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既然是三部曲我就要坚持这种叙述方式,在《桃花》中也是采取这种方式。如果连叙述方式都改变了,那还叫三部曲吗?
3、 关于法律和文学。我用文学的书写方式,不断地去挑逗这些身处法律中的人们,把他们推到欲望的边缘,让这些研究生,这些法官,律师,让他们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而这些人的游戏生活又一直都在冒犯法律。但奇怪的是,因为情节的合情合理,是可信的,很多人又觉得他不违法。所有人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安然度过,活着还很有滋味,这其实就是当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正如陈晓明先生所说:“这些文学的不可信又和法律文本的可信结合起来,也就是严肃的不可信性和可信的不严肃性,在法律的背景下书写,意味深长。”其实,我就是希望用文学的不可信去挑战法律的可信,用文学的光芒照亮法律的黑暗角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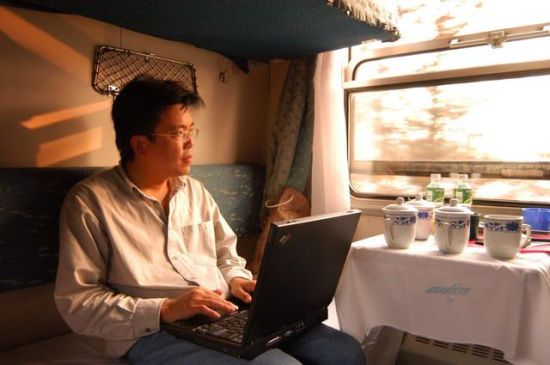
张者:用文学的光芒照亮法律的黑暗角落
《桃夭》是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要找个批评家审读,就找到孟繁华老师,他给我提了3000字的意见,我看了修改意见有点犯傻,在床上打滚,思考着这怎么改呀,然后又给孟繁华打电话,在电话交流中我突然豁然开朗,也就是说他把我这盏灯点亮了,后来稿子经过了一次大的改动。当然,目前看来《桃夭》还有修改的余地,其实,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每一本书总是要留下一点遗憾,不留下一点遗憾,今后的写作怎么完美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了今后的完美,就暂时留下点遗憾吧。
不过,我还是想就各位老师的一些看法回答如下:
1、 关于小说中的巧合。在写作中我确实采用了一些巧合,采用这些巧合时我当然不能用所谓的“无巧不成书”来安慰自己,我也知道情节的过分巧合可能降低故事的可信度,从而消解小说的艺术性,可是我还是采用了很多巧合,我的目的恰恰不是为了让读者可信,是为了让读者不信,在不可信中产生一种荒诞感。其实,所有的巧合都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时发生。比方:我叫张波,我在读大学时曾经认识了一位也叫张波的女生,我们两个差点成为恋人,如果成为了恋人,而且还结了婚,生了孩子我肯定起名叫张小波。看吧,这是发生在我自己生活中的事,这很巧合,巧合得已经不可信了,就达到了荒诞的效果。
请不要把我的作品当纯粹的现实主义作品来阅读。巧合的极致就荒诞,荒诞的极致是魔幻。我想完成一种城市的荒诞现实主义。对,就命名为荒诞现实主义吧。
2、 关于人称叙述。有人认为小说中的这个“我”身份没有严格遵守叙事视角的客观性,如一个幽灵的存在。其实,这种叙事方式不是我的首创,早在80年代莫言先生在《红高粱》中就采用了这种叙事方式,我奶奶,我爷爷……按照叙事视角的客观性原则,就视角来说,我怎么能看到我奶奶和我爷爷过去的事情?猛一看是第一人称叙述,其实又不是第一人称叙述,说是第三人称叙述,又时不时出现一个“我”。这个“我”有时在情节中存在,有时又不在情节中。我把这种叙述方式叫“双人 称”叙述方式。
张者:用文学的光芒照亮法律的黑暗角落
早在《桃李》的写作中,我就采用这种方式了,当时也有朋友和我探讨过这种叙述,会不会有悖叙述伦理。《桃夭》的主要叙述人“我”是五个师兄弟中的一位,但叙 事视角并不仅仅停留在“我”这里,而是在“我”和五个师兄弟之间互相自由地转换。“我”似乎游离于圈子之外,又似乎不断地介入到每一个切身感受当中,与他们交谈,与读者对话。通读整部小说,“我”似乎是一位能穿梭时空的叙述者,“我”的叙述可以穿越历史,回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个纯真诗意的理想年代,并在历史和现实中自由穿行。毫无疑问,这叙述方式使得小说的叙述背景更为辽阔深远,使人物更加立体丰满,能更好地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既然是三部曲我就要坚持这种叙述方式,在《桃花》中也是采取这种方式。如果连叙述方式都改变了,那还叫三部曲吗?
3、 关于法律和文学。我用文学的书写方式,不断地去挑逗这些身处法律中的人们,把他们推到欲望的边缘,让这些研究生,这些法官,律师,让他们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而这些人的游戏生活又一直都在冒犯法律。但奇怪的是,因为情节的合情合理,是可信的,很多人又觉得他不违法。所有人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安然度过,活着还很有滋味,这其实就是当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正如陈晓明先生所说:“这些文学的不可信又和法律文本的可信结合起来,也就是严肃的不可信性和可信的不严肃性,在法律的背景下书写,意味深长。”其实,我就是希望用文学的不可信去挑战法律的可信,用文学的光芒照亮法律的黑暗角落。
[ 编辑: 何雯 ]



























